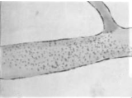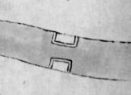由于现存文献阙如,因此关于胶莱运河开凿及其运营历史的研究长期难以深入。图说作为目前胶莱河流域最早、最详尽的水文调查资料,记载了胶莱河支流汇入之口133处、水深数据29条、水闸8座、烟墩20处、桥梁1座、庙宇3座,保存了明后期胶莱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信息,这对于复原胶莱河开凿与通航的历史、理解明代频繁出现的恢复胶莱河议案均有重要价值。
运河是两条自然河流间的人工水道,而分水岭的存在,意味着运河水道必有上坡或下坡。因此运河的关键工程有两个,一是水道上的节制工程,二是水源供给工程。据《元史》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张君佐“率新附汉军万人,修胶西闸坝,以通漕运”
②(②《元史》卷一五一《张荣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582页。)。这证明元代胶莱河上已有节制闸,但其详情缺载。王献曾计划修复胶莱河上的闸坝以恢复胶莱河航运,但这一工程因其在嘉靖十七年(1538)调任山西任布政司左参政而未能完工。
③(③樊铧:《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万历三十年实勘胶莱河所见节制闸数量为8座,其中陈村闸、周家庄闸、玉皇庙闸、杨家圈闸已倾颓,吴家闸尚存乱石踪迹,窝铺闸、亭口闸与新河闸保存较好。海仓一带注“无闸”(
图2),并对水文环境有所描述:“北海口至海仓口三十余里,东西无岸,俱淤沙、漩泛,如遇东北大风,海水泛涨。”
④(④《北海口至新河闸图》注文,1725年,编号: gm71005020,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可知这一带已属河口环境,河流与海洋在此交汇,呈现“东西无岸,俱淤沙”的景观。
关于胶莱河的水源问题,万历三十年实勘记录证明,当时胶莱河通航的最大障碍是流域水量不足。通过对山东菏泽出土的元代内河单桅货船的复原研究,可知该船设计吃水为0.8米,船底板和外板的列数与明代《南船纪》所载一百五十料船完全一致。
⑤(⑤龚昌奇、张启龙、席龙飞:《山东菏泽元代古船的测绘与研究》,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编:《航海——文明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据此推测胶莱河通航水位应不低于0.8米,即水深不少于二尺四寸。
⑥(⑥元明两代一尺长约34厘米。参见卢嘉锡主编,丘光明等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7—408页。)根据
表2,胶莱河除在靠近莱州湾的吕桥至北海口间水深有二至四尺,其他河段水深均不足二尺。周家闸至窝铺闸间水深多在一尺左右,地势最高的窝铺闸至吴家闸间是胶莱南河与北河的分水岭,多数河段呈无水状态。吴家闸以南河段水深大多不足一尺。胶河不再像元代那样,先注入湖泊再流入运河
①(①杨霄:《元代胶莱河的形成及其在河海联运中的作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3年第1辑。),而是直接注入胶莱河,未经湖泊调蓄的河水含沙量较高,且水量不稳定,导致“流沙随泊水冲淤,反为河害,难以挑筑”
②(②《周家闸至亭口闸说》,1725年,编号: gm71005020,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 分图名称 | 河 段 | 水 深 | 河床与河岸 |
| 北海口至新河闸 | 北海口至道儿港十里余 | 二三尺 | 无岸约束 |
| 道儿港至赵家河十一里余 | 二尺 | 细沙难挑,不能筑岸 |
| 赵家河至窝落二里许 | 一尺五寸 | 沙淤难挑,平漫无岸 |
| 窝落至闸口五里 | 水稍深 | 微有岸迹 |
| 闸口至龙王庙三里 | 三尺 | 泥沙难挑 |
| 龙王庙至姚家庄三里 | 东水深一尺,西水深二尺 | 河二股,沙卤难挑 |
| 新河闸南至杨家圈闸 | | 三四尺不等 | 堪成河身 |
| 杨家圈闸南至玉皇庙闸 | 杨家圈上至吕桥、下至新河闸 | 二三尺不等 | 堪成河身 |
| 吕桥至玉皇庙 | 一尺三五寸不等 | |
| 玉皇庙闸南至周家闸 | 玉皇庙 | 水浅 | 内多乱石 |
| 曹家沟外 | 水浅 | 两岸倶土崖 |
| 白塔沟外 | 水浅 | 河身下有碙𥐾石 |
| 周家闸南至亭口闸 | 周家闸 | 一尺五寸 | |
| 大成店 | 一尺 | |
| 杜家道口 | 一尺五寸 | |
| 董家口外 | 一尺 | |
| 亭口闸南至窝铺闸 | 亭口闸 | 二尺 | |
| 指张口 | 一尺一寸 | |
| 窝铺闸西 | 水微 | 沙多 |
| 窝铺闸即分水岭闸至吴家口闸 | 白河口东 | 无水 | 淤沙 |
| 杜家庄道口 | 水少 | 沙多 |
| 杜家庄道口以东河段 | 水少 | 两岸堤高,有碙𥐾石 |
| 吴家口闸以西 | | 多碙𥐾石 |
| 吴家口闸至陈村闸 | 小沽河岔 | 四寸 | |
| 赵家村泊水口以西十余里 | | 皆碙𥐾石 |
| 夏家口 | 五六寸不等 | |
| 杜家口 | 三四寸不等 | 河底俱碙𥐾石,且有大者 |
| 刘家闸子 | 五六寸不等 | 沙 |
| 赵家口 | 水少 | 俱碙𥐾石 |
| 韩家口 | 二三寸不等 | |
| 陈村闸至胶州海口 | 陈村闸 | 七八寸不等 | |
由图说记载可知,万历三十年的实勘还进行了筑坝蓄水试验。在周家闸附近的杜家车道口拦水筑坝时,“水止深一尺五寸,五日后,水长五寸,至十日并无消长;迤南至董家口建坝,原水一尺,十日后,并无消长;又迤南一坝为亭口,原水二尺,十日后,并无消长;又查周家闸迤南,为大城店,原水一尺,蓄止十日,亦无消长”③(③《周家闸至亭口闸说》,1725年,编号: gm71005020,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据高密县报称:“自亭口至指录口建一坝,原水一尺一寸。十日后,水消一寸。又迤南至王干坝为一坝,原水五寸,十日后水消一寸。又迤南至窝铺为一坝,原水一尺,十日后水消一寸。”④(④《亭口闸至窝铺闸说》,1725年,编号: gm71005020,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窝铺迤东为贤家庄泊水口,迤西为刘家庄泊水口。迤东而南,则由杜家庄、张家庄、孙家口、谭家庄、刘家村至吴家口一带,水几断流,无可实验。⑤(⑤《窝铺闸即分水岭闸至吴家口闸说》,1725年,编号: gm71005020,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可见当时胶莱河水源不足,即使有闸坝节制工程,大多数河段仍达不到通航条件。
万历三年刘应节与徐栻提出借胶河通海运,被朝廷寄予很大期望。刘应节所主张的开“胶莱新河”并非要恢复元代旧河,而是另择“便道”①(①刘应节所谓的便道为胶州南自淮子口大港头出海,由州治而西,抵匡家庄,约四十里,俱岗沟黄土,宜用挑治。自刘家庄北抵抬头河、张奴河,至亭口闸三十里,俱黑泥下地,水深数尺,宜用挑浚。自亭口闸历陶家崖、陈家口、孙店口,至玉皇庙约六十里,河宽水浅宜从旧河之旁另开一渠。玉皇庙至杨家圈二十里,水势渐深,约五六尺,宜量行疏浚。杨家圈以北,则悉通海潮,无烦工程矣。大抵此河以工力计之,宜开创者什五,挑浚者十三,量浚者什二;以地势论之,宜挑深丈余者什一,挑深数尺者什九。参见〔清〕顾炎武撰,黄坤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7页。),而这一便道最大优势就在于成本低廉。按照刘应节的估算,“以万夫之力,兴数月之工,掘地止数十里,所费仅数万金”②(②〔清〕顾炎武撰,黄坤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第3册,第1758页。)。工部意见也认为:“今议改于城南便道,工力不多,经费又省。”③(③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三年九月甲寅”条,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页。)
徐栻出发前往山东勘视前已被赋予了很大的处置权力,“所有未尽事宜,悉听尔以便宜行事,大小官员从宜委用,有应改用者奏请改任”。圣旨还提到:“今利害既审,断在必行,有阴持私见、造言阻挠,及承委官员托故推避者,悉听尔指实参奏,拿来重处。”④(④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三年九月甲寅”条,第117页。)即便如此,这次开胶莱河议案最终仍在山东抚按官的强烈反对下停罢。以往研究多认为山东当地官民反对开河是畏惧工程所带来的“科派之扰”①(①樊铧:《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第175—176页。)。在徐栻往山东计处开浚事宜的时候,张居正给他的书信中提到:
胶河之可开,凡有心于国家者皆知之。乃竟为浮议所阻者,其端有二: 一则山东之人,畏兴大役,有科派之扰。又恐清渠一开,官民船只,乘便别行,则临清一带,商贩自稀,此昔年之说。一则恐漕渠既开,粮运无阻,将轻视河患,而不为之理。此近年之说也。②(②〔明〕张居正:《张太岳集·书牍》卷七《答河道徐凤竹》,中国书店2019年版,第147页。)
可见当时就有这种传言。但其矛盾在于,万历三至四年的这次胶莱河议案最初就是由山东地方官员发起,张居正在给山东巡抚李世达的信中也曾提及:
向承教胶河事,时方议凿泇口,未遑论也。今泇口既罢,刘、徐二司空复议及此,适与公议合,故特属之,望公协恭熟计,共济此事。③(③〔明〕张居正:《张太岳集·书牍》卷七《答山东抚院李渐庵言吏治河槽》,第148页。)
以山东巡抚李世达为代表的山东地方官员早在刘应节与徐栻复议海运之前就已有开胶莱河的意向,且嘉靖年间王献开马家濠的行动也完全由山东地方出资主导,显然山东地方官民对开胶莱河始终抱有很高的积极性,因为胶莱新河一旦开通,将对当地贸易发展有一定助益。依万历《即墨志》载:
至若议开新河,则县之西陈村、栾村数处,即商贾贸迁之所。议行海运,则县之东刘村、王村一带,即鱼米交易之乡,此百姓无穷之利,三齐转泰之机。④(④万历《即墨志》卷一〇《艺文》,《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33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66页。)
但刘应节实勘胶莱河后提出的开河方案却遭到李世达、商为正等山东地方官员强烈抵制,并最终导致议案停罢。面对李世达的转变及其与刘应节的各执一词,因以往多为夹杂政治因素的非客观材料,无法评估当时技术条件下开通胶莱河的可行性。⑤(⑤樊铧:《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第327页。)现将图说中的记载置于万历三四年间胶莱河议案的背景下,并与刘应节与李世达等人的言论对照,可对此议案停罢的原因有新的认识。
谈九畴所总结的“三阻”之论,其实恰好概括了刘应节与李世达争论的三个核心问题。关于是否应开古路沟以避积沙,谈九畴在图中标注了“尚书刘委守备丁珠试工未就处”⑥(⑥《陈村闸至胶州海口说》,1725年,编号: gm71005020,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其西有大沽河岔水,横冲带沙,入河淤塞,旋挑旋淤,工无所施。他进一步指出“今欲开河行舟,势必先由麻湾淤滩,次鸭绿港、石落湾等处,及陈家闸以上达分水岭。无论分水岭之高之远,即以麻湾至陈家村数十里,其间险石淤沙,从古无能为力”⑦(⑦《陈村闸至胶州海口说》,1725年,编号: gm71005020,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可见刘应节所称建新闸工程并未完工,原因是自然条件无法满足施工要求,他所宣称的“潮水流通,浮沙不入”⑧(⑧〔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卷一二二《运河水》,《中国水利史典·二期工程·行水金鉴卷》第2册,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20年版,第1057页。)并非事实。
关于北海口是否存在淤沙,图说记载“据勘,北海口至沙湾三里,水浅无岸。沙湾至道儿港七里余,水虽稍深,无岸约束。道儿港至赵家河十一里余,水深二尺,细沙难挑,不能筑岸。赵家河至窝落二里许,水深一尺五寸沙淤难挑,平漫无岸。窝落至闸口五里,水又稍深,微有岸迹。闸口至龙王庙三里,水深三尺,泥沙难挑。龙王庙至姚家庄三里,河二股,东水深一尺,西水深二尺,沙卤难挑”。根据实地试验,“由海沧闸往北起至窝落铺,兴工三日,势宽阔。夫役脚底难以存立,随筑随淤,难以成功。恐涉推诿,严行再筑试验。已于四月初一等日,勉强并工,筑成二坝,忽遇初十日大风偶起,将前二坝随水推去。则以潮来势猛,非人力所能胜也”①(①《北海口至新河闸说》,1725年,编号: gm71005020,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可见李世达所言非虚,刘应节预设工程在北海口同样无法实现。
关于分水岭是否应疏浚、借潮通航是否可行,图说首先说明刘应节试凿工程的结果:“挑深一丈九尺,长二十丈,竞以下多碙𥐾石与浮沙,又以掣水甚难而止。自以开试后,今沙积反高于前,水不东南流矣。”②(②《窝铺闸即分水岭闸至吴家口闸图》注文,1725年,编号: gm71005020,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然后根据实地勘测所见指出:“据勘得高、平、昌、掖、胶五处,皆颓然四低,惟分水岭其翘然最高埠者,由岭而俯视,胶东之地其高不可寻丈计。况以南海之深,视岭悬绝,挑之极深。引水上注,更欲直通北海,使两海通贯,纵深计六丈,宽计一十余丈。度理与势,未知能济否?”③(③《窝铺闸即分水岭闸至吴家口闸说》,1725年,编号: gm71005020,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可见要实现借潮通航,至少要将分水岭挖深六丈,但试挖一丈九尺后即难以再挖。
《汇辑》中保存的万历三十年实勘记录证明,万历四年刘应节所主张的施工方案在当时无法实施,这也是李世达据理反驳刘应节的直接原因。但在徐栻踏勘胶莱河并提出工程方案时,却未见山东抚按官提出任何异议。这是由于徐栻到达胶莱河后即修正了刘应节的方案,《明史·河渠志》称:“应节议主通海,而栻往相度,则胶州旁地高峻,不能通潮,惟引泉源可成河。”④(④《明史》卷八七《河渠五》,第2141页。)万历四年元月,徐栻勘河后建议疏凿黄阜岭以北、分水岭以南的船路沟,并称此地“地形平衍,水势浸漫,且旁有可济之河水,有可引之源泉。其上流为姑、胶等河,浚之以为血脉;其下流为张奴等河,浚之以为经络。各建闸座以通其咽喉,广开水柜以滋其荣卫,立堤塍以障其流沙,开月河以泄其溃溢”⑤(⑤〔清〕顾炎武撰,黄坤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第3册,第1759—1760页。)。谈九畴在图说中肯定了徐栻这一方案,称:“昔尝有议建置水柜、水闸为障沙蓄水之术者,良工心独苦矣。” ⑥(⑥《窝铺闸即分水岭闸至吴家口闸说》,1725年,编号: gm71005020,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可见山东当地官员的真实意愿是建造有水柜和节制闸的传统运河工程。但按照徐栻的估价,工程需要耗资百万,中央与地方均无力承担,刘应节的借潮水通航方案又不具备可行性,因此即使山东地方官员向来主张重开胶莱河,也只能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