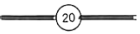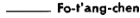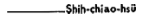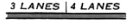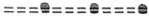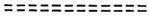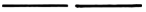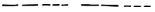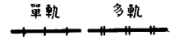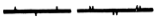此处所指中国地形图时间有两层含义: 一是出版时间,即地图本身的历史;二是所绘内容的时间,即地图所载地物信息呈现的历史。后者在历史地理研究中更为关键。
版本上看,L500中仅地形图NG 49-16与NH 45-16为第二版,其余241张均为第一版。L542中第一版有51张,第二版有44张,集中分布在北纬48°以南至中朝边界、东经120°以东至中朝、中苏边界地区,第三版有5张,分布在中朝边境地区。L594中除NG 51-3为第二版,余者均为第一版。由于朝鲜战争,东北地区地图版本的更新频次高于其他地区,区域内部亦存在差异。朝鲜战争的战线一度直逼鸭绿江,美国军机更是轰炸安东等地,中朝边境地区作为战区,地图版本更新频次最高。其次是中朝边界后方300—500千米的纵深地带。东北其他地区更新频率则与关内一致。
中国地形图从编制到出版历时弥久。L500的编制始于1952年,止于1958年;出版始于1954年,延续至1965年。近六成地图开始编制于1954年,65%出版于1957—1959年。其中出版周期最短者仅4个月,耗时最长者近12年,平均编制出版时间为5.4年,近六成在5年内完成。L594的编制集中在1950—1951年,出版集中在1953年。L542的编制始于1950年,止于1959年;出版始于1951年,止于1963年,有42张编制于1950—1951年,41张为第一版;48张编制于1955—1956年,43张是第二、三版;有44张出版于1957—1959年,均为第二版;41张出版于1963—1964年,均为第一版。L542有大量第二、三版地图,编制周期出现明显分化,平均编制周期为6年半,但近半地图编制时间在3年以内,其中80%是第二、三版;35张编制时间在12年以上,均为第一版。若由此认为第二、三版地图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编制,速度快于第一版,则存在“幸存者偏差”。换句话说,现存第二、三版地图对应第一版的编制速度不一定慢于第二、三版。目前并未看到第二、三版地图对应第一版的实物,第二、三版最早编制于1954年,说明第一版甚至部分第二版在1954年前已编好。实际上,因第二、三版地图以第一版为蓝本编制,故其地图说明会透露第一版的版本信息,部分还会写明编制时间、地图质量。此类第二、三版地图的初版中,有28张出版于1950年,20张出版于1951年,因其编制时间都在1950年,故此类地图均在一年内出版。
综上所述,朝鲜战争初期,美军即对我国东北全境做出地图出版的规划。毗邻中朝边界的东北近半地区的地图出版于开战后的一年内,并在停战不久后更新,而靠近中苏边境地区的地图编制速度较慢。整体上看,朝鲜战争的战线相对稳定后,美国开始重视绘制中国大陆地形图,停战后即开始大规模绘图。
中国地形图非完全实测图是根据已有各比例尺地图改绘并据航测图像加以修正的成果。其编制与出版时间代表了地图的制造时间,并非所载地物信息的时间。地物信息时间的确定,在有航测修正区域应据航测时间判定,无航测修正区域应据底图时间判定。
如
图3所示,除L594系列航测时间集中在1946—1949年间外,另两个系列的航测多在1944—1945年。长江以南的航测时间早于长江以北,重庆政府直接控制的西南大后方区域则最先完成了航测。航测数据集中分布在沈阳—昆明轴线以东地区,这也与中美合作航空测量队的活动区域相符。
图3 中国地形图航测时间示意资料来源: 根据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图书馆藏中国地形图L500、L542、L594系列之地图说明整理。 |
如
图4所示,1944—1945年,就各区域地图航测覆盖率而言,重庆政府直接控制的西南地区最高,多数地图在50%以上。位于敌后的华北地区在50%以下;东北地区不仅航测覆盖率低,且时间断限不明。东南沿海地区部分地形图中,陆地部分航测率近100%,但整体航测率却较低,或是因图中地区海域占比高,中美双方航测不足。可见航测覆盖率与重庆政府控制能力直接相关。
图4 中国地形图航测覆盖率示意资料来源: 根据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图书馆藏中国地形图L500、L542、L594系列之地图说明整理。 |
需指出的是,仅部分地形图做了航测修正,而这些图亦非所有区域都经过了航测修正。在未修正的区域,各地形图所据底图仍是判定地形图内容时间的重要依据(
表2)。
表2 中国地形图底图发行机构、图幅数量和时间 (单位: 幅) |
时间
机构
| L500 | L542 | L594 | 合计 |
| A | B | C | D | E | A | B | C | D | E | A | B | C | D | E |
| 美国空军制图局 | 0 | 14 | 52 | 14 | 3 | 0 | 2 | 1 | 1 | 1 | 0 | 0 | 0 | 0 | 0 | 88 |
| 美国海军测量局 | 1 | 12 | 18 | 34 | 2 | 0 | 6 | 8 | 4 | 5 | 0 | 0 | 1 | 7 | 0 | 98 |
| 美国陆军制图局 | 0 | 35 | 14 | 1 | 2 | 0 | 1 | 0 | 55 | 0 | 0 | 3 | 0 | 1 | 2 | 114 |
| 日本参谋本部 | 0 | 33 | 0 | 0 | 2 | 21 | 131 | 0 | 0 | 45 | 0 | 3 | 0 | 0 | 3 | 238 |
| 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 | 0 | 25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25 |
| 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部 | 0 | 3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3 |
|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 0 | 0 | 0 | 0 | 0 | 0 | 21 | 0 | 0 | 2 | 0 | 0 | 0 | 0 | 0 | 23 |
| 日本水文图 | 1 | 3 | 0 | 0 | 0 | 0 | 0 | 0 | 0 | 1 | 0 | 1 | 0 | 0 | 0 | 6 |
| 英国海军部 | 2 | 0 | 0 | 5 | 3 | 0 | 0 | 0 | 0 | 0 | 0 | 1 | 0 | 0 | 0 | 11 |
| 印度测量局 | 1 | 8 | 3 | 0 | 6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18 |
| 法国水文图 | 0 | 0 | 0 | 0 | 2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2 |
| 中国参谋本部测量局 | 9 | 3 | 0 | 0 | 5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1 | 18 |
| 四川陆地测量局 | 0 | 3 | 0 | 0 | 3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6 |
| 情报数据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7 | 0 | 0 | 0 | 0 | 3 | 0 | 10 |
| 苏联红军参谋部 | 0 | 0 | 0 | 0 | 0 | 0 | 1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1 |
| 远东司令部 | 0 | 0 | 0 | 0 | 0 | 0 | 0 | 1 | 0 | 0 | 0 | 0 | 0 | 0 | 0 | 1 |
| 野外注记摄影主要平面特征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4 | 0 | 4 |
| 现有最优中国地图 | 0 | 0 | 0 | 0 | 187 | 0 | 0 | 0 | 0 | 1 | 0 | 0 | 0 | 0 | 0 | 188 |
| 合计 | 14 | 139 | 87 | 54 | 215 | 21 | 162 | 10 | 67 | 55 | 0 | 8 | 1 | 15 | 6 | 854 |
| 注: 本表时间指底图发行时间,为1931—1936年(A)、1937—1945年(B)、1946—1949年(C)、1949—(D)、其他(E)。 资料来源: 根据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图书馆藏中国地形图L500、L542、L594系列之地图说明整理。 |
各比例尺底图是中国地形图的数据来源。底图合计854张,其中L500有509张,L542有315张,L594有30张,其显著特点是源流众多、比例尺不一、出版时间跨度大。其出版机构可考者有652张,共15家。按国别分,美制地图、日制地图各占底图总量的35%,另有22%的底图为现有最优中国地图。
讨论中国地形图的内容时间,有必要对占底图多数的美制地图、日制地图进行更详细的分析。美制地图主要发行机构为陆军制图局、美国海军测量局和美国空军制图局。美国空军制图局的地图多为1:25万的航空测量图,发行时间主要集中在1946—1949年,覆盖区域大体在中国西部以及湘南、赣南等地,这与美国空军二战期间在华的活动范围大致相当。美国海军测量局的地图为水文图,近半发行于1949年后,具体测量时间不可考。陆军制图局所绘底图情况较为复杂,L500中的底图多来自L531、L532、L581、L582四个系列。
以L500的NG 47-3 为例(
图5),根据地图说明和图料表可知,该图绝大部分区域根据1946年编制的L582系列G 47 D及G 47 E(
图6)绘制。将NG 47-3与G 47 E同方位局部图面比较可知,虽然
图5对山体做了阴影处理,但其等高线走向及间距与
图6仍极为相似。河流走向皆为自南向北,
图5与
图6中走向几乎一致的较粗虚/实线为摩托化行进道路,稍有不同的是
图5原图中用红色将重要道路突出,其他用黑色绘制,
图6则都使用的红色线型。两图中聚落皆用小圆圈表示,与
图6相比,
图5仅多出母古地、大西等聚落地名。可见NG 47-3确以G 47 E为底图,并在其基础上增加了标注地物。前文已述,L542中的底图是该图的初版,初版编制时间都在1950年。当时,东北地区已非由美军控制,美军难以更新数据,故初版地图应与第二版类似,参照民国时期的日制地图编制而成。
日制地图主要发行机构为日本参谋本部、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行均在1945年前。L500系列底图主要为参谋本部发行的1:5万和1:10万两类地图,1:5万地图内容多为南京、芜湖附近地区,地图说明标明了底图图番号。据此与《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的地图比较,可确认它们系日本根据1939—1941年的航测数据绘制。如NI 50-12(淮安)图所记“日本参谋本部民国三十一年制南京五万分一地形图”,即1942年日本参谋本部空中写真测量《中支那五万分一南京四十二号》“蒋坝”。根据任玉雪等的研究,这批地图属于《空中写真测量要图》,乃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航测所得,地图分幅和整体架构借鉴过之前民国实测地图。
①(①任玉雪、邓发晖:《<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所收地图来源分析》,《历史地理研究》2020年第3期。)1:10万地图内容多为东部沿海地区,在1944年左右编制。L542系列依日本参谋本部发行的底图绘制的地图占总量六成以上,时间跨度大,分布范围广,其中最主要的类型为1:10万地图。“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盗测;“九一八”后,日本又攫取大量东北地区地形图及地图底版;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参谋本部将这些地图改绘成1:10万地图。
①(①许哲明:《从<接收日制图版目录>解析日军侵华制作之中国地图》,Blogger[2019-3-12],
https://sjm460405.blogspot.com/search/label/%E6%97%A5%E8%A3%BD%E5%9C%B0%E5%9C%96%E7%B3%BB%E5%88%97%281%29。)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又对东北地区全面测量,绘制了一批1:10万地图,1937—1945年的底图数据皆来于此。譬如NK 51-8(沈阳)曾参考1932年日本参谋本部编制的《满洲十万分一图奉天十五号》1:10万地形图“抚顺”。1920年东三省陆军测量局曾印制《奉天省抚顺县附近第一千零六十三号》1:10万地形图“抚顺县”。将两者图面相比较,所示地域差别较大,制图风格也有明显差别。日军图将抚顺南北的山脉走向用等高线连续详尽地画出,而东三省图虽也使用等高线,但并不密集,未将山势连续画出。NK 51-8中抚顺附近的等高线是较为连续详尽的,这显然与东三省图不符。
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编制的底图仅存在于L500系列,比例尺为1:10万,主要涉及山陕、豫西地区,在1938—1943年发行。该系列地图实际是1937年前我国编制出版的1:5万地形图的缩小复制。
以宏道镇、横山村两个较大聚落点为例,中国地形图中这样的四等城市通常用圆点表示,用色块的情况很鲜见。
图7展示了NJ 49-8局部,该图地图说明指1940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编制《山西省十万分之一地形图》的“忻县”图(
图8)是其底图之一。比较两者同位置图面可见,
图7中有宏道镇、横山村用色块展示了形状大小,并有公路连接;
图8也有这两处的形状,以及连接二者的公路。 1936年中国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出版的1:10万地形图中也有这两个聚落,但均用圆点表示,无形状面积绘出。又据“忻县”之图备考可知,该图是日军根据虏获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缩小调制,按照中国1914年图式。将“忻县”图与1934年中国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出版的1:5万地形图(
图9)“宏道镇”同位置比较,“忻县”图除各图标较“宏道镇”图有缩小外,内容高度相似,甚至等高线走向与数量都基本一致,且“宏道镇”也是按1914年图式编制。由此,可认为NJ 49-8的部分原始数据可上溯至1922年。
中国地形图中绘制时以当时可见最优(best available)中国地图为底图的占有相当大比例,尤其是L500系列,但地图说明未指明这些底图的发行单位、时间和番号,只说明其比例尺大小,故难以确切对应相关底图内容,只能根据史料推测。L500中近77%都选用了当时可用的最优底图,这些底图几乎全为大比例尺,仅有10%的地图参考过中比例尺地形图。西南、西北地区使用的多是“最优”底图。根据史料,AMS在20世纪50年代持有的中国大比例尺地形图大致有三类: 前文所述L781等一系列AMS编1:5万地形图,原始数据是我国的1:5万地形图;根据《中美合作航空测量合同》和《中美合作航空测量合同》所获我国大比例尺地形图;日本投降后美军缴获的日本编制地形图。①(①[日]小林茂:《外邦図——帝国日本のアジア地図》,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第247—249页。)这些地图大部分同源,均系我国的测量数据,而部分大城市及其周边如香港、上海、北京、南京、汉口则可能以GSGS所绘大比例尺地图为底图①(①L781中香港地区陆地部分是以1932年GSGS出版之1:2万地形图为底图。又,1945年AMS曾翻印GSGS在1927年出版的重要城市大比例尺地形图,可见AMS也掌握部分英制地图。),故所谓“最优中国地图”大部分源数据仍是我国测绘所得。
根据中国地形图的航测数据与底图数据可知,中国地形图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地理状况。从时间上看,大陆地区的航测数据集中在1944—1945年,台湾地区在1946—1949年。基于美制地图的大部分陆地区域,其数据时间在1925—1945年。基于日制地图的区域,东北以外的大陆地区为1937—1945年,甚至更早,东北地区为1931—1945年。从空间上看,航测数据集中在沈阳—昆明轴线以东地区,航测覆盖率自西南向东北逐步降低。底图为美国空军制图局地图的区域集中在西南地区,为美国陆军制图局地图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底图为日制地图的区域主要在华北、华东、东北等沦陷区。底图依据“最优中国地图”所绘地图分布较广,但其核心使用地域在西北、西南地区。
中国地形图的航测数据和底图数据时间大多在1945年之前,反映的是民国时期的地理状况。但该图编制于1949年之后,1946—1949年的地理信息、1949年之后的地物信息,又是否有所表达?鉴于行政区划和重大工程是军用地图应着重记载的地物要素,以二者为依据,可进一步判断地图内容时间。
中国地形图标出的省级行政区划边界是考证内容时间的重要依据之一。根据L542的索引图和图幅接合表可知,该系列将中国东北地区划为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东北九省是国民政府抗战后在东北施行的省级行政区划。1949年后,东北的省级行政区划开始合并,至L542各地图成图时,原东北九省已并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L500上画了北平、西安、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民国时期院辖市的边界范围,考虑到西安、广州迟至1947年6月才设为院辖市②(②《国民政府令》,《国民政府公报》第2845号,1947年6月7日,第1版。),而西安、南京、广州、重庆在该区域地图成图时应已取消直辖市地位,因而从区划上看,中国地形图基本反映的是全面抗战爆发后至1949年前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划。
该套图中的长沙机场、榔梨市和成渝铁路情况也颇具代表性,探究其变动能更好把握所绘内容的时间。NH 49-16图(1953年编制,1958年出版)根据当时最优的大比例尺度地形图编制,地物则按1944年航测修正。长沙机场在已见民国各版大比例尺地形图中位于城北大圆洲,但大圆洲机场在抗战后期被毁,并未重建。日军占领长沙后,将城东协操坪辟为机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又加以扩建。1951年,协操坪机场改建为体育场;1952年,城南大托铺兴建新机场。如
图10所示,地图所标机场(左上横线处)即协操坪机场所在。该图无大圆洲机场却有协操坪机场,说明美军应根据1944年的航测结果和情报修正过,但该图编制时协操坪机场已改建体育场,大托铺机场也于1954年竣工,说明美国和台湾当局都不清楚这一消息,地图内容停滞在1949年。比长沙机场更明确的依据是长沙县治所在地。1949年7月长沙县人民政府在金井成立,8月迁榔梨市,同月长沙和平解放。1950年3月长沙县政府迁潘家坪, 1996年迁至今星沙镇。地图中的长沙县治标注于榔梨市,说明国民党在长沙解放前后数月间尚能获取相关情报,待湖南局势迅速稳定后,此类情报未再更新。
成渝铁路1950年开工,1952年竣工通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早在1936年成渝铁路就已完成勘测,并断续的施工,至1949年前已完成部分占工程总价的14%①(①成渝铁路工程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成渝铁路工程总结:工程设计部分》,成渝铁路工程总结编辑委员会1953年版,第1页。),内江以东准备铺轨。1949年后,内江以东部分仍基本用原来的路基建设,内江以西部分,特别是成都至乱石滩段则进行了改道。②(②成渝铁路工程总结编辑委员会编:《成渝铁路工程总结:工程设计部分》,第7—9页。)中国地形图中绘制有成渝铁路的地图,由西向东分别是NH 48-6(1958年编制,1963年出版)、NH 48-10(1957年编制,1963年出版)、NH 48-11(1958年编制,1964年出版)、NH 48-12(1954年编制,1964年出版),这四张地图的数据多源于抗战期间中国绘制的大比例尺地形图和航测数据。
此四图还未编制时成渝铁路就已建成通车。后三图中铁路都以单线画出,无其他注释。仅在NH 48-6图中,成都至乱石滩段也按单线画出,但在旁注明“APPROXIMATE ALIGNMENT”(近似对准),即与成渝铁路实际走向或有一定差距。成渝铁路建成后,媒体报道大量涌现,后来还出版了“成渝铁路工程总结”丛书,美军可由此获得铁路使用原线或改道的情报,但改道部分美方无法实地勘测,故进行了加注。中国地形图对成渝铁路的表现方式,清晰表明其地图内容以1949年为界存在分野。
区划治所和机场铁路等工程具有极高军事价值,是军事地图必不可缺的内容,但受制于情报,中国地形图并未及时更新信息。中国地形图基本将1949年前的信息绘出,1949年后的大部分信息则只能依靠少量情报绘制,或直接空缺,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行政区划调整几乎完全忽视。结合前述重大工程绘制情况可知,在航测数据和底图数据的基础上,美军也利用情报对1946—1949年间的地物变动进行过修正,即中国地形图的内容和时间反映的是抗战后至1949年前的中国地理情况。因此,该图作为近代中国的详细地形图,对于中观尺度的历史地理研究而言是较为理想的材料。